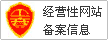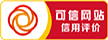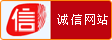广州窗帘培训:这大概是元庆末年或仁和初年的事了。是哪个朝代对这个故事本身,倒也影响不大。读者只要知道约是平安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就可以了。当时的摄政王藤原基经手下的武士中,有某位正五品武士。这大概是元庆 末年或仁和 初年的事了。是哪个朝代对这个故事本身,倒也影响不大。读者只要知道约是平安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就可以了。当时的摄政王藤原基经手下的武士中,有某位正五品武士。本不想写“某位”,想详细介绍一下其生卒年等生平事迹,但不巧的是,在旧传之中没有记载,大概是个没有资格立碑树传的平凡男人。著旧传之人似对凡人俗事兴致不高,这一点倒和日本的自然派 作家有着天壤之别。王朝时代的小说家都非空闲之人。总之,在摄政王藤原基经手下的武士之中,某位五品武士正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五品其貌不扬。第一,五短身材,另加酒糟鼻子,耷拉着眼角。嘴上胡须天生稀疏。脸颊瘦削,尖嘴猴腮,嘴唇是……不胜枚举。这位五品武士的容貌简直是天生的猥琐龌龊。五品是何时、如何成为基经的手下,无人知晓。但他总是身着同一身褪色的短衫,头戴同一顶干瘪纱帽,不厌其烦地做同一件事,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是确凿无疑的。结果,如今谁见了都不会想到这个男人也曾经年轻过(五品已经四十开外了)。相反,觉得他生来就是一副冻得通红的鼻子、虚有其名的胡子,在朱雀大街上让大风摧残。上至主人基经,下至放牛的孩童,都无意识地觉得理所当然,无人质疑。一个人长成这样,受到的待遇概不用说,大家也能想象到。一同供职的同僚也对五品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连那些没有级别的二十多个最下级武士也对他的出入,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极度冷淡。对于五品的吩咐,他们仍然是谈笑风生、置若罔闻。于他们而言,五品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最下级武士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上面的官员也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也是他命中注定。他们中的多数对五品都是冷峻的神情后隐藏着小孩子的恶作剧一样,无论吩咐什么事情都只做个手势。人类之所以有语言存在,这绝非偶然。因此,手势不能传达其意之事时有发生,但他们都认为是五品的悟性上存在缺陷。于是一旦手势不能交流时,他们便从五品干瘪变形的纱帽,到脚上快磨破的草鞋跟,不停地上下打量,然后鼻子一哼,转身就走。尽管如此,五品却从未生气。他是一个对一切的不公平都无动于衷、浑浑噩噩、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他的那些同僚武士,却得寸进尺地对他百般捉弄。年老的同僚取笑他相貌丑陋,不厌其烦重复着那些老套的桥段。年轻的同僚也借此机会插科打诨。他们在五品面前,对他的鼻子、胡子、纱帽、短衫乐此不疲地评头论足。不仅如此,五六年前就和他分开的地包天嘴唇的老婆,以及和他老婆鬼混的酒鬼和尚,也经常成为他们的笑料。他们还变本加厉地搞些性质恶劣的恶作剧。现在已经无法一一列举了。列举一个把他的竹筒酒喝掉后另灌上尿的事例,窥一斑而见全豹,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五品对于这些捉弄浑然无动于衷。至少从旁观者看来,他好像是浑然无动于衷。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面不改色,一声不吭地边摸着稀疏的胡须,边做该做的事情。只有在他们的捉弄实在是过分的时候,例如,把纸条别在他的发髻上,在他的长刀鞘上绑上草鞋,他才会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不要这样啊,你们。”看到这副表情,听到这样的求饶,无论谁都会在刹那间,被激起恻隐之心(被他们欺负的,不止是红鼻子的五品自己,还有素不相识的很多人——这些人都借着五品的表情和求饶,来谴责他们的冷漠无情)。这种感觉虽然朦胧,却在他们的心头,瞬间蔓延开来。但能始终保持这恻隐之心的人却屈指可数。在这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中,有一位没有品位的武士。他来自丹波国,是一个嘴上长着毛绒胡须的年轻人。当然,这个年轻人也和大家一样,毫无理由地对红鼻子五品表示鄙视。但是有一天碰巧听到了“不要这样啊,你们”这句话,这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自此以后,在他眼中,五品判若两人。从五品营养不良、面无血色、呆若木鸡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饱经社会蹂躏的“人”。这个没有品位的武士,每每想起五品的经历,就感到世间的一切,突然显露出原来的卑劣龌龊,与此同时,五品被冻得发红的鼻子和数得过来的胡子,带着一丝安慰依稀传到他心头。但是,这仅限于年轻人一人而已。除他之外,五品依然生活在周围的蔑视之中,不得不像狗一样继续生活。首先,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黑色短衫和一条同颜色的裤子,已被洗得发白,变得既不蓝又不藏青。短衫的肩膀处有些松松垮垮,圆形纽扣和衣服边角连接处的颜色也都变得怪怪的。裤子底边也破烂不堪,裤子中央往下没有衬裤,露出瘦细的腿,即使不是毫无口德的同僚,看他这样瘦牛拉着破车的样子,也觉得他太过寒碜。而他佩戴的长刀也不伦不类,刀柄把手已坏,黑色刀鞘的涂漆也斑驳陆离。他却依旧红着鼻子,趿拉着草鞋,在凛冽的寒风中,本就弓着的腰越发猫了下来,像找什么似的左顾右盼,在街上一步一挪。连大街上卖东西的小商贩都对他捉弄戏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近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五品去神泉苑,经过三条的小门时,看到有六七个孩童聚在路旁,不知在玩什么。五品心想,是在玩陀螺吗?于是他从后面偷偷瞄了瞄,原来他们在殴打一只脖子上拴着绳子,迷了路的多毛狗。胆小懦弱的五品,虽然一向怀有同情之心,但总是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从没敢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但此时面对的是几个孩童,他心中不禁涌现几分勇气。他笑呵呵地拍拍一个貌似孩子王的孩童肩膀道:“饶了它吧,狗挨打也痛呀。”这时,孩子王转过身,翻了翻白眼,轻蔑地瞥了瞥五品,那神情酷似侍卫长官与他无法交流时的样子。“别多管闲事。”孩子王后退一步,傲慢地反唇相讥,“你想干什么?你这个红鼻子。”五品觉得这话就像一记耳光抽在自己脸上,但不是因为受到辱骂而感到生气,而是因自己多管闲事,自讨没趣感到极其窝囊。他只好用苦笑掩饰,一言不发地继续向神泉苑方向走去。后面的孩童们,六七人搭着肩膀,对他伸着舌头,做鬼脸,翻白眼。当然,五品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就算知道,对窝窝囊囊的五品来说,又能如何呢?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只是为了让人戏耍羞辱而生在世上,另外没有任何人生希望吗?倒也未必。五品从五六年前开始就对山药粥异常执着。所谓山药粥,是将山药切碎,用地锦的汁液熬成的粥。这在当时作为无比的美味佳肴,甚至摆到了万乘之君皇帝的御膳之中。因此,像五品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一年一度大摆宴席的时候才能品尝得到。不过,即使是那个时候,也只够润润喉罢了。于是,一直以来,能够饱饮山药粥就成了他毕生唯一的愿望。当然,他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愿望,不,就算是他自己也从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他毕生的愿望。但毫不过分地说,事实上他就是为这个而活着——人类,有时会为了一个根本不知能否达成的愿望,而付出毕生的精力。笑其愚蠢的人,终究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但五品梦寐以求的“能够饱饮山药粥”这个愿望,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现实。个中原委,正是这个山药粥故事的目的所在。有一年的正月初二,正是基经府邸大摆宴席 的日子(和中、东两宫的宴席同一天,摄政·关白 宴请大臣以下的公卿,和两宫的宴席规格伯仲之间)。五品也夹杂在做客的那些武士之中,面对着那些残羹冷炙。当时那个年代,还没有取食 的习惯,剩饭都是让家里的武士,汇聚一堂,共同分享。虽说可以媲美两宫的盛宴,但终究是在古代,品种虽然很多,但鲜有稀有的东西,只是些年糕、蒸鲍鱼、鸡干、宇治的小鱼、近江的鲤鱼、嘉吉鱼、鲑鱼子、章鱼烧、大虾、大芦柑、小芦柑、橘子、柿子等,其中就有刚刚提及的山药粥。五品每年都盼着这个山药粥,但每次都是僧多粥少,能喝到他嘴里的,少之又少,且今年粥的量又少得可怜。也许正因为稀少,他觉得格外美味。喝完后,他直勾勾地盯着空碗,用手抹了抹粘在稀疏胡子上的残粥,自言自语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喝个饱呀?”“大夫 竟然从没有饱餐过山药粥吗?”一个磁性威严、颇具军人风格的声音嘲讽地打断了他的话。五品抬起深埋的头,怯生生地向他望去。声音来自同在基经府中任武士的民部卿时长的儿子藤原利仁。他虎背熊腰,膀大腰圆,一边嚼着板栗,一边不停地举着盛满黑酒 的酒杯。人已经酩酊大醉。“真可怜呀。”利仁看到五品抬起了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说道,“如果你想的话,我利仁可以让你喝个够。”平常就算是一条饱经摧残的狗,给块肉也不容易亲近。五品照旧是窘迫得满脸堆笑,目光不停地在利仁的脸上和空碗之间徘徊。“不想?”“……”“如何?”“……”五品能感觉到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稍有疏忽,肯定又会招致众人的嘲笑捉弄。或者说,无论怎么回答,最终还是会被众人捉弄戏耍。他进退两难。如果不是对方有些不耐烦地喊道了句“不想就算了,也不强求”,五品的目光估计会一直在碗和利仁之间徘徊不停。他听到这些话后,惊慌失措地答道:“不,恭敬不如从命。”
听到这个回答,大家一时间不禁哄堂大笑。“不,恭敬不如从命。”——甚至有人还鹦鹉学舌地模仿着五品的回答。在盛放橙黄、橘红的盘子和台子上,众多的软硬纱帽都齐声哄笑,笑声如同破浪般向远方传去。其中,最为大声、最开怀大笑的就是利仁本人。“那么,我改天请你。”他边说边皱起了眉头,是因为涌上来的笑声和酒气都噎在喉咙里。“……可以吗?”“恭敬不如从命。”五品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又把前面的回答重复了一遍。当然,这次不必说,又招来笑声一片。至于利仁,正是要让五品重复一遍,所以才故意这样问,因此他比刚才更加夸张地晃动着宽阔的肩膀,捧腹大笑。这个朔北的莽汉,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开怀畅饮,二是开怀大笑。但是,所幸的是谈话的中心,即将从这两个人身上离开。外面的人就算是玩笑逗乐,都一起集中在五品身上,也可能招致别人的不快。总而言之,话题由此及彼地轮换,酒和菜肴临近尾声之时,有一学徒武士骑马把两脚都插进一条皮护腿里的笑话,引得众人兴趣盎然。但只有五品,对场上的笑话,无动于衷。大概“山药粥”三字,已牵动了他所有的神经。面前的烤山鸡,他也不动一筷子;面前的黑酒,他也不喝一口。他只是两手放在膝盖上,如同相亲的姑娘般,连霜染的双鬓都红了,始终直直地盯着黑漆空碗,傻傻地微笑着。那之后又过了四五天,一日上午,两个静静骑着马的男人沿着加茂川河岸,行走在粟田口的街道上。其中一人是个虬髯大汉,佩戴长刀,穿着深蓝色官服,下身是同颜色的裤子。另一人,破旧的蓝黑短衫上又罩了一件薄棉的外衣,是位四十几岁的武士,腰带系得松松垮垮,红鼻子上还流着鼻涕,浑身上下处处都流露着非常寒酸破败。但二人的坐骑,前一位是桃花马,后一位是三岁的黄白相间的金钱马,引得路上的小商贩和武士都纷纷驻足回头相望。后面的两人,紧随马匹之后的自然是马弁和随从了——这就是利仁和五品一行的故事,不必特意细说。虽说是冬天,倒也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白色河岸的石头间,潺潺溪流岸边的蓬蒿叶子都纹丝不动。临河低矮的柳树,没有叶子的枝头上,洒满了柔滑似饴的阳光。树梢上踩着一只鹡鸰,不停地抖动着尾巴,影子清晰地倒映在街道上。暗绿的东山上像被霜打过的天鹅绒一样的山头,那完全露出来的大概就是比睿山吧。马鞍上的螺钿在刺眼的阳光下,流光溢彩。两人不挥一鞭,慢悠悠地向粟田口的方向驶去。“请问,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五品怯生生地拉着缰绳问道。“马上就到了,就在前面不远处。”“是去粟田口附近吗?”“嗯,差不多。”今日一早,利仁说东山附近喷涌着温泉,邀请五品一同前去。红鼻子的五品信以为真,恰逢好久没有泡温泉了,身上奇痒无比,前几日刚吃过山药粥,又来泡温泉,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幸福。他稍一盘算,就跨上利仁牵来的金钱马,但一同来到此处才发现,利仁并非真的想要来这里。现在,他们已经不知不觉中走过了粟田口。“不是到粟田口的吗?”“别废话,继续往前走,你呀。”利仁面带微笑,故意不理睬五品,静静地打马前行。两侧的人家,渐渐稀疏起来。现在广袤的冬日原野上,只能看见觅食的乌鸦,山北逐渐消残的积雪上像是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青烟。虽然晴空万里,尖锐的漆树树枝直插天空,让人觉得非常刺眼,望而生寒。“那么,是要去山科那边吗?”“山科在这里,我们还要往前走呢。”果然,交谈之中就已过了山科。不光如此,不知不觉中,关山也落在了身后。终于在晌午时分,一行人来到了三井寺。三井寺内有一僧人和利仁私交甚笃。两人前去拜访,并叨扰了一顿斋饭。饭后,两人又策马急行,一路上感觉,比起前面走过的路,更加人迹稀少。尤其当时那个年代盗贼四处横行,时局动荡。五品越发地弓起他的驼背,仰头向利仁问道:“还要往前走吗?”利仁微笑着,就像小孩子的恶作剧被大人发现后向大人微笑的样子。他鼻梁上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似乎在犹豫是笑,还是忍住不笑。终于,利仁开口道:“其实,我是想把你带到敦贺。”利仁边笑着,边用马鞭指向远方。马鞭的下面闪烁着午后近江湖反射的粼粼波光。
五品惊慌失措。“敦贺?难道是越前的那个敦贺?那个越前的……”利仁自从做了敦贺人藤原有仁的女婿后,多半时间都住在敦贺,这五品倒是偶有耳闻。但是,居然要把自己带到敦贺,直到如今也不敢想象。首先,要翻山越岭前往越前国,却只带着两名随从,如何保证沿途的安全呢?而且,最近过往路人被强盗劫杀的谣言也不时耳闻——五品面露难色地望着利仁。“那也太不靠谱儿了,以为是去东山,不料是山科。以为是去山科,岂料是三井寺,最后竟然是越前的敦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开始便说是到敦贺,那么随从也要多带几名——敦贺,这也太不靠谱儿了。”五品几乎哭出了声,小声地嗫嚅道。如果不是“饱饮山药粥”的诱惑一直支撑着他,恐怕他早已就此作别,独自回京都去了。“有我利仁一人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路途上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看到五品如此狼狈不堪,利仁皱着眉头,嘲讽道,随即叫来随从,把带来的弓箭壶背在身上,又拿来一张黑漆真弓,横放在马鞍桥上,催马前行,一骑绝尘。既然事已至此,胆小怕事的五品,也只能唯利仁马首是瞻。五品心惊胆战,不停打量周围荒凉的原野,口中念念有词,重复着快要忘记的几句观音经文,红鼻子几乎都要蹭到马鞍前桥了。他随着摇摇晃晃的马步,踉踉跄跄地向前方驶去。在马蹄回声阵阵的原野上,漫山遍野都长满了黄茅。一处处的水洼积水,冷冷地倒映着蓝天,令人不由暗忖这个冬天的下午,怕是会永久地凝固住了。原野的尽头,连绵起伏的山脉,大概是背光的缘故,光彩夺目的残雪也失去了光芒,蓝色的暗淡色调延伸向远方。就这也被有些衰败的枯草所掩盖。很多景象,是两个步行的随从看不到的。就在这时,利仁猛地回头,对五品叫道:“那里,来了一个好使者,可以向敦贺报信啦。”五品不太明白利仁话的意思,心惊胆战地顺着弓指的方向望去。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在野葡萄或者是别的什么藤蔓缠绕交错的灌木丛中,只有一只暖洋洋毛色的狐狸在落日的余晖中,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狐狸惊慌地跳起身,夺路而逃。利仁急忙扬鞭策马开始去追。五品也不顾一切,紧随利仁其后,拼命追赶,随从当然也不能落后。须臾之间,马蹄踩踏石头的急促声打破了旷野的寂静。不久,见利仁已经勒马停蹄,正提着不知何时已捉住的狐狸后腿,倒挂在马鞍桥边。想必是追赶得狐狸走投无路,只能在马下束手就擒。五品慌忙不迭地抹着稀疏胡须上的汗水,终于骑马赶到跟前。“哎,狐狸,给我好好听着。”利仁将狐狸高高地提到眼前,故意像煞有介事地说,“告诉他们,今晚,敦贺的利仁要打道回府了。就说利仁现在在陪同一位贵客,明天巳时,在高岛附近,派人前来迎接,还要准备两匹配鞍的好马。知道了吗?不要忘了。”说完后,利仁一甩胳膊,将那狐狸远远地丢进草丛中。“呀,快跑,快跑!”好不容易追赶上来的两名随从,顺着狐狸逃跑的方向望去,一边拍手,一边叫嚷道。只见那个畜生枯叶色的后背在夕阳之中,不顾树根和石头,慌不择路,落荒而逃,从五品一行人的位置上看,尽收眼底。在追逐狐狸的时候,不知何时,他们来到了一处旷野的缓坡和干涸的河床相连的地方,那里还稍稍有些高度。“真是个宽宏大量的施主呀。”五品不禁肃然起敬,由衷慨叹着,对着这个连狐狸都能够指挥自如的莽汉的脸,重新仰视了一番。自己和利仁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这样的事情他是无暇考虑的。他只是强烈地感受到,只要利仁的意志能够支配的范围越大,在那个意志里面,自己的利益就越大——阿谀奉承,恐怕在这种时候,被最自然地流露了出来。读者今后如果从红鼻子的五品的态度中看到些卑躬屈膝的东西,千万不要光凭这个就对这个男人的人格妄加怀疑。被扔出去的狐狸,顺着斜坡滚落下来。在干涸的河床的石头中间,它小心敏捷地飞跳过去,冲着对面的斜坡,一鼓作气地跑了上去。它边跑还边回头看徒手抓获自己的武士等一干人,他们还在远方那个斜坡上,列马排在一起。他们看上去只有手掌大小,特别是在落日的余晖中,桃花马和金钱马在寒霜的空气中,比画像还要鲜明,像雕刻一般凸显出来。狐狸将头一扭,又在枯草之中,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而去。一干人等按照计划,第二天巳时抵达高岛附近。这里面朝琵琶湖,是个小小的村庄,与昨天大相径庭,在阴霾的天空下,几户茅草屋,稀稀落落地散开;岸边生长的松树间,泛着涟漪的灰色湖面像忘记打磨的镜子般,萧索开阔——来到此处,利仁对五品扭头说道:
“看那里,他们已经列队相迎了。”果然有二三十个男人,有的骑马,有的徒步,牵着两只配好鞍缰的马,上衣的衣袖在寒风中飞舞,从湖岸松林间急匆匆地飞奔而来。转眼间就到了眼前,骑马的都慌忙下马,徒步的都蹲跪在路旁,毕恭毕敬地等候利仁的到来。“果然,看来那个狐狸真去通报了。”“生性变幻莫测的畜生,那种营生,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五品和利仁谈话之间,一干人等已来到家臣们等候之处。“太隆重啦。”利仁说道。蹲跪的家臣们,慌忙站立起来,接过二人的缰绳。顿时,众人都兴奋起来。“昨天晚上,有件稀奇古怪之事。”两人下马之后,刚要往皮垫之上落座,一个穿着黄红色短衫的白发家臣来到利仁的面前说道。“是什么?”利仁把家臣们拿来的美酒和菜肴,一边给五品斟满,一边大模大样地问道:“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戌时刚过,夫人突然神智不清,说‘我是阪本的狐狸。今次特地来传达主公吩咐的事情,都上前来好好听令’。于是,我们一同前往参拜,夫人又说道‘主公正在陪同一位贵客,正在归来的途中。明日巳时,在高岛附近,派人前去迎候,去时带上两匹配好鞍缰的好马’。”“是够稀奇古怪的啊。”五品仔细地看着利仁,再看看家臣,讨好似的阿谀奉承道。“不仅如此,夫人还惊恐万分,浑身颤抖地说:‘千万不要怠慢,如有怠慢,我会被主公逐出家门的。’此后夫人浑身瘫软,痛哭流涕。”“那么,后来又如何了?”“后来,夫人就一下子晕厥过去。我们出门时还未苏醒。”“怎么样?”听完家臣的禀告后,利仁看着五品,得意扬扬地说道,“利仁连畜生都能吩咐自如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呀。”五品一边揉着红红的鼻子,一边略低下头,故意装傻充愣,瞠目结舌。胡子上还沾着刚才喝的酒。当天夜里,五品躺在利仁府中的一间房里,茫然地望着那盏方形灯台。他辗转反侧,漫漫长夜无心入眠,好容易才等到天明。傍晚到达此地之前,和利仁以及他的随从一路谈笑风生,经过松山、小河、枯黄的原野,还有草、树叶、石头、野火的烟——这些东西,都一一浮现在五品心头。终于,他们在这暮色霭霭之时,来到府中。支起的长炭箱子中,炭火的火焰熊熊燃烧,看到此情此景,他终于放下心来——且现在自己竟然躺在这里,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仿佛是极远古之事。五品在四五寸厚棉花的直垂衾 下,心满意足地伸着腿,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睡姿。直垂衾里是利仁借给他的淡黄色厚棉衣服,穿了两层。仅是如此,也足以暖和得让他发汗,加之晚餐时,他喝得微醺的缘故,当下更觉燥热。枕头旁的屏风对面,是霜色遍地的宽阔庭院,于是,五品陶醉其中,丝毫不感到一点痛苦。这里所有的一切,和京都自己住的屋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尽管如此,不知何由,我们的五品心中仍然七上八下,略感不安。首先,时间的流逝慢得令人发慌,而同时,天亮则意味着要喝山药粥了,天不要亮得太快。这两种矛盾的感情相互交织,境遇的急剧变化,使他局促不安,就像今日的天气般,突然变得寒冷难耐。这些全都是烦恼,以致来之不易的温暖也没有引起五品丝毫的睡意。这时,外面的庭院之中传来很大的叫嚷声。听声音,似乎是今日在中途迎接他们的白发家臣在吩咐指示着什么。那干涩的声音,可能是经霜后回声的缘故,变得威严冷峻,字字都好像要穿透他的骨髓。“这边的人听着,奉主公之命,明日一早,卯时之前,每人要上交粗三寸、长五尺的山药一根。都记好了,卯时之前。”重复了两三次后,人声戛然而止,又像之前一般,恢复了冬夜的寂静。在这寂静之中,方形灯台的油吱吱作响。红色棉线般的火苗,不停地颤抖。五品忍住了即将打出的一个哈欠,又开始了胡思乱想——既然说到山药,那肯定是要拿来做山药粥的。这样一想,刚才只顾注意外面而暂时忘记的不安,不知何时又重新涌上心头。而且,比刚才更加强烈的是,不想过早就能喝饱山药粥的心情,竟然恶作剧似的在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如果这么容易就实现了“饱饮山药粥”的夙愿,那么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这么多年来的隐忍岂不是都白费了吗?如有可能,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小意外,暂时喝不成山药粥,然后,意外解除,下次历尽艰难险阻,一次喝个够——这样的想法,就像陀螺一样,咕噜咕噜地在原地旋转之际,五品因一路的舟车劳顿,沉沉地酣睡了过去。翌日清早,一睁开眼睛,就想起昨晚上的山药之事,五品先打开房间屏风向外看,一看才知道,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睡过了卯时。宽阔的庭院之中,铺了四五张长席,上面都摆满了又粗又长的东西,大概有两三千根,有斜刺出来的桧皮葺 屋顶那么高,堆积如山。定睛一看,全都是三寸粗、五尺长的大个山药。五品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目瞪口呆地望着四周。宽阔的庭院里新打的桩子上,并排放着五六个能装五斛米的大锅。着白色衣服的年轻侍女,几十人在忙碌着,有的烧火,有的掏灰,或从崭新的白木桶里向大锅里加地锦汁 ,大家都在为山药粥做准备,正忙得热火朝天。大锅下的烟、锅里冒出的蒸气和还未消失殆尽的晨雾融为一体,庭院里一片模糊,看不清东西。在一片雾蒙蒙中,红彤彤的是锅底熊熊燃烧的烈火,眼前所见所闻就像是战场或者火灾现场一样,嘈杂万分。五品此时不禁思考,用这样巨大的山药,这样巨大的能容纳五斛米的大锅,来熬山药粥。而自己,只是为了吃山药粥,从京都特意长途跋涉来到越前敦贺,越是思考就越觉得自己可怜。我们五品那值得同情的食欲,实际上此时已经减少了一半。又过了一小时,五品和利仁,还有利仁的岳父有仁共进早餐。跟前放了一个带提梁的银锅,装得像海水一样满,似乎快要溢出来的就是那可怕的山药粥。五品刚才看到,那堆积至房檐高的山药,被几十个年轻男子用快刀麻利地从一头快速切碎。那些侍女往来穿梭地将切碎的山药一个不剩地都放在可装五斛米的大锅中。最后,那成山高的山药,一个不剩地从长席上消失的时候,几道混合着山药香味和地锦汁香味的热气,从锅中袅袅升起,在早晨晴朗的天空中,向上飞舞。对于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五品来说,对着锅里的山药粥,还没有品尝,就已经觉得饱了,这也不无道理。五品在锅前窘迫地擦着额头的汗水。“你不是从来没有喝饱过山药粥吗?快请,别客气,使劲喝吧。”岳父有仁吩咐侍从,另外再摆上几口银锅。每一锅山药粥,都快要溢出来了。五品闭着眼睛,红鼻子此刻越加鲜红。他将银锅里的半数山药粥都盛在大泥碗中,硬着头皮喝光。“家父说了,千万不要客气。”利仁在一旁,不怀好意地笑着,劝他再喝一锅。吃不消的是五品。不客气地讲,从一开始,他就一碗也不想喝。现如今,他一再强忍着,才勉强喝掉半锅。再喝下去的话,恐怕没等咽下喉咙,就要吐出来了。但不喝的话,等于是辜负了利仁的一番好意。于是,他又闭上眼睛,喝光了剩下一半的三分之一。此时,他连一口也喝不下了。“谢谢盛情款待,不胜荣幸。呵呵,不胜荣幸。”五品语无伦次地说着。此刻他简直是狼狈不堪,胡子上、鼻子上,完全不像是在冬天,不停地滴答着汗水。“这吃得也太少了,客人太客气了,哎,你们还等什么呢?”侍从们听从有仁的吩咐,又从银锅中向泥碗中舀山药粥。五品像是驱赶苍蝇般地不停挥动着双手,表示拒绝。“不喝了,已经喝饱了。不好意思,已经喝饱了。”如果不是利仁突然指着对面屋檐说“快看那里”,利仁恐怕还会不停劝说五品,让他喝山药粥。但幸运的是,随着利仁的一声吆喝,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对面的房檐上。早晨太阳的光芒洒在桧皮屋顶葺上,在那刺眼的光芒中,一只毛皮油光水亮的畜生,老老实实地蹲坐在那里。定睛一看,正是昨天利仁在旷野之上徒手捉住的那只阪本的狐狸。“快看,狐狸也要喝山药粥呀。来人哪,快给它吃的。”听了利仁的命令,从屋顶上跳下的狐狸,径直奔向院子中间的山药粥,开始大快朵颐。五品望着喝着山药粥的狐狸,心中依依不舍地回想着从前的自己:那个被众多武士戏耍捉弄的自己;被京城的孩童骂“干什么,你这个红鼻子”的自己;穿着褪色的短衫、裤子,像丧家之犬般徘徊在朱雀大街上那个可怜孤独的自己;但同时又将饱饮一顿山药粥的愿望珍藏在心底的、幸福的自己——他为终于不用再喝山药粥而感到安心,同时也感觉到,满头大汗渐渐从鼻尖开始变干。虽然晴空万里,但敦贺的早晨仍然有些寒风刺骨。五品慌忙捂鼻子的同时,冲着银锅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大正五年八月
信息来源:广州窗帘培训 新时代窗帘培训